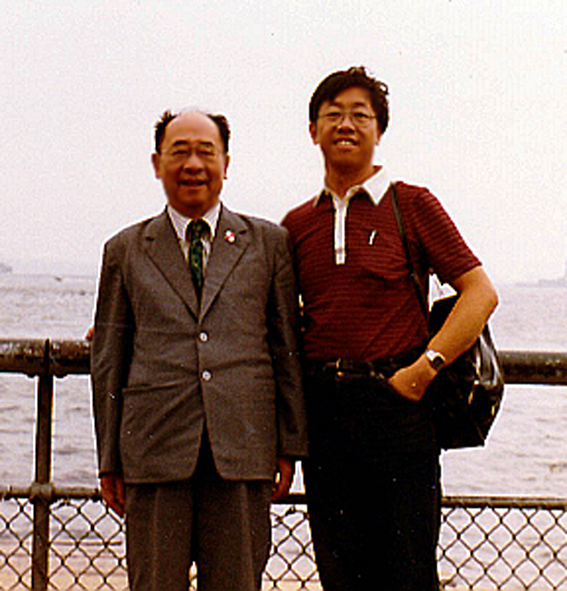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之一是四五岁时,那时父亲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他常常在遇到难题时,坐在沙发上,一边想问题,一边用食指与中指在沙发的靠手上交替敲着,久了,靠手上敲出两个指印来。傍晚,他累了,常常带我去散步。那时我家住在清华大学北院,穿过北门到清华校园墙外,经过一片农田,可以走到一条铁路旁。沿着铁路线旁的小路散步时,他常常给我讲些趣事。比如火车离我们很远,还看不见时,可以趴在铁轨上先听见它的声音。又如火星上有可能有生物,又讲到白矮星上一个米粒大的东西比地球上的卡车还重……每当回想起那走在父亲身边的时刻,总是感到十分亲切、幸福。晚霞、铁路、农田与父亲讲述的故事,构成了我童年的美好回忆。
1952年,父亲怀着兴奋的心情带着全家到东北创建东北人大物理系(现永利总站62111物理系)。记得在从北京去往长春的火车上,我看见一个个电线杆向后掠去,就问父亲:一切都向后移动,那么打开收音机时,电台的位置是不是也动呢?父亲想了一下便告诉我,是不动的,因为只移动很小距离,小到完全看不出来。
父亲创建的物理系充满生机,学生思想活跃。每逢过年,组织学生各做一个小表演实验。比如我还记得有一个两只眼睛是用灯泡做成的小人,手上放着一个盒子,你伸手去取盒子里的糖时,还没有碰到任何东西,小人的两只眼睛就亮了,还发出一个叫声,十分有趣。
父亲是一个十分豪爽的人,朋友很多,家中经常高朋满座,父母也常常带我去看朋友。聊天中海阔天空,我也喜欢听。记得父亲常常谈起当时物理系的兴旺时期,但生物学发展很快,再过二三十年,生物学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正是DNA发现后的几年,从那里父亲已看出来生物学的前景。跟父亲在一起时总是愉快的。
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家中朋友骤然减少,寥若晨星。父亲常去新华书店外文部买书(原来父亲告诉我他在划为右派后买了许多书是因为他担心以后因为成了右派,查书查资料会遇到困难)。那时我已上初中,他常常带我去新华书店与外文部买书,从外文部出来,父亲就陪我去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好书。我对天文学有兴趣,有一次看到一本大学天文学教科书,我很有兴趣,但那毕竟是大学教科书,我不知当买不当买,父亲鼓励我,可以买,看不懂可以慢慢学嘛!后来这本书果然对我很有影响,对于行星的轨道为什么是椭圆的一部分需要关于微分方程和牛顿力学的知识,我看了此书,果然看不懂,却知道了要学什么才能看懂。
我在喜欢天文学的同时,也开始喜欢无线电。从矿石收音机开始。到了初中,开始想自己装电子管收音机,但不会焊接。父亲知道了说:这个不难,我来教你。我第一次焊接零件就是这样从父亲那里学来。现在每当我焊接什么零件时,就会想起当年父亲是怎样教我的。
我在中学时是学俄语的,进了大学也只能上俄语班,而一进大学父亲就叫我自学英文。他说:“你学了英文,整个世界就在你面前打开了。”父亲没有找英文教科书来教我,只是教了我26个字母,然后说:“可以了,我找本物理书给你看吧。”他找了一本Sears的普通物理让我看。我一个一个单词地查字典,硬着头皮看。几个月后,我觉得收获极大,我已经可以看一些其他书了。父亲的引导对我的前途起了关键的作用,是极有远见的。因为我在大学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就发生了,图书馆经常关闭,借不到书,我靠父亲书架上的英文书学完了四大力学一直到量子场论。我还到新华书店外文部订了很多集《物理评论》,这些对我走向科学的道路起了关键作用。
我的英文水平提高到能看外文书,是父亲被下放到伊通县的时候,那时我被分配到了靖宇县。他找了一本旧的英文版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对我说:“就用这个学。”我带着这本书回到靖宇县,慢慢地读。英文很难,有时所有的词都查出来了,可还是不懂什么意思。放假回伊通县时,我就坐在父亲身边看这本书。他在做研究,我看不懂就问他,经常打断他的工作,他从不厌烦,每次都给我讲得很清楚。每想到这些,总使我深深地怀念我慈爱的父亲。
当“文化大革命”进入派性斗争时,我和父亲都有较多的空闲时间,我开始学习量子力学。我用父亲的书,既学英文,又学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关于波函数的统计解释很难理解。我问父亲:怎么这样难懂?他告诉我这本来是一个没有完全弄清楚的基本问题。我记得我们晚上关了灯躺在床上(那时我们家一共只有一间屋子),我与父亲说了很久。我终于明白了即使是经典名著上讲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完全解决了的问题,也不一定是对的,我可以有自己的理解。父亲从不迷信权威,他鼓励我独立思考。父亲讲了他对波粒二象性的看法。他当然知道这只是一个想象,完全不一定对。但是这使我了解了科学家与学者的区别。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不仅只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使我懂得学习不只是为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创造,更富有想象力。这些话引起了我对量子力学的极大兴趣,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去学越来越多的东西。中国科学院的何祚庥先生曾写道:“余瑞璜教授是位卓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将一位弟子领向量子力学之门。”我对这句话是有深深的体会的。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偏远的靖宇县教中学,那里没有科研条件,我感到前途茫茫,对学习粒子物理与量子场论的前景十分悲观。父亲劝我:“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不仅用诸葛亮的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来安慰我,还鼓励我说:“可以跟我学金属学、结晶学。”于是我就在私下按照父亲的指导读了许多结晶学和固体物理的书,甚至实验物理方面的书也看了,后来父亲搬回长春,我放寒假回家看父亲,每次借许多书和杂志回去看,这段学习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父亲讲过许多科学史上的生动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父亲对待科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常常想起父亲讲的关于法拉第的两个故事:父亲参观过法拉第的实验室,看过他写的笔记,他说最深刻的印象是法拉第关于电磁感应的笔记。法拉第做了很多年关于电磁感应的实验,每一页上都写着“no”,即“没有效应”失败了。但他不灰心地做了好多年,终于在最后一页上用很大的字写了“yes”,即成功了。另一个故事是法拉第报告电磁感应定律成功时,一位贵妇人问他:“这又有什么用呢?”他回答说:“夫人,您怎能预料一个新生婴儿的未来呢?”
父亲讲的另一个故事也给我很大启发。父亲在英国留学时遇到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曾和波尔熟悉。他说波尔当时有了原子模型的想法后,到英国来寻求有名科学家的支持。他首先找到的是汤姆森,但汤普森对此不感兴趣,使波尔感到苦恼。这位教授就对波尔说:“汤姆森对原子模型有自己的想法,与你不同,他不会感兴趣的。但卢瑟福正在考虑原子模型,与你的想法很相似,你为何不去找他?”后来波尔的理论果然得到了卢瑟福的支持。
我对父亲的敬仰不只因为父子亲情和他在科学上对我的引导,更因为他的为人。父亲心胸坦荡,热情奔放。他是一个打不倒的人,即使是被人踩在脚下,他从不认为比别人低一等。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一次在永利总站62111礼堂鸣放宫看电影。坐在他旁边的一个曾经被父亲提拔起来的教授看见他看电影时哈哈大笑,冷冷地说:“当了右派,还笑什么?”我父亲说:“我高兴为什么不可笑?”后来说起此事,他对我们说:“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不可以笑!”
“文化大革命”时,父亲再次受到打击。有一次,父亲正蹲在一个学生宿舍厕所的地上用小刀清理便池上的尿垢,一个学生过去莫名其妙地打了父亲一掌。父亲生气地站起来说:“人家老老实实在干活,你为什么打人?”那人说不出话来,瞪眼看着父亲。一下围上不少人,那人恼羞成怒,又打了父亲一下。父亲就又提高了嗓音重复了那句话。四周的人越围越多,但都沉默不语,这样对峙了一阵以后,人们才散开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体会到,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能有这种勇气,保持做人的尊严,有多么不容易。
香港一家报社曾在1948年以“英雄教授”为标题,赞扬我父亲在外国海轮上为中国人打抱不平的正义行为。父亲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父亲非常佩服诸葛亮,他常常唱起杜甫歌颂诸葛亮的诗:“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并笑着手指天上对我们说:“你看诸葛亮多高,正像很高的白云中的一根羽毛。”
父亲这一生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都是满怀希望向前进。父亲常常引用法拉第的名言“满怀希望向前进,比达到还好。”有位教授不理解这句话,认为没有达到怎么会比达到还好。但我从生活中深深地理解父亲的这一信念。父亲多年来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在1992年已经86岁时还对我说,他希望再活10年来完成他的工作。可惜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他这种总是满怀希望向前进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
余理华
1998年年初写于美国
选自《结晶——余瑞璜传》附录
作者简介:
余理华,余瑞璜的次子,永利总站6211169届毕业生,永利总站62111客座教授。